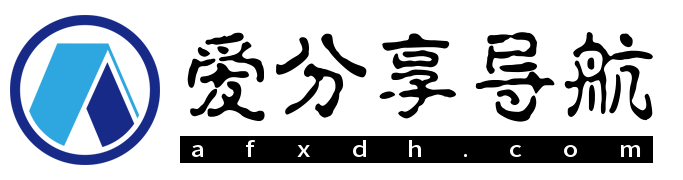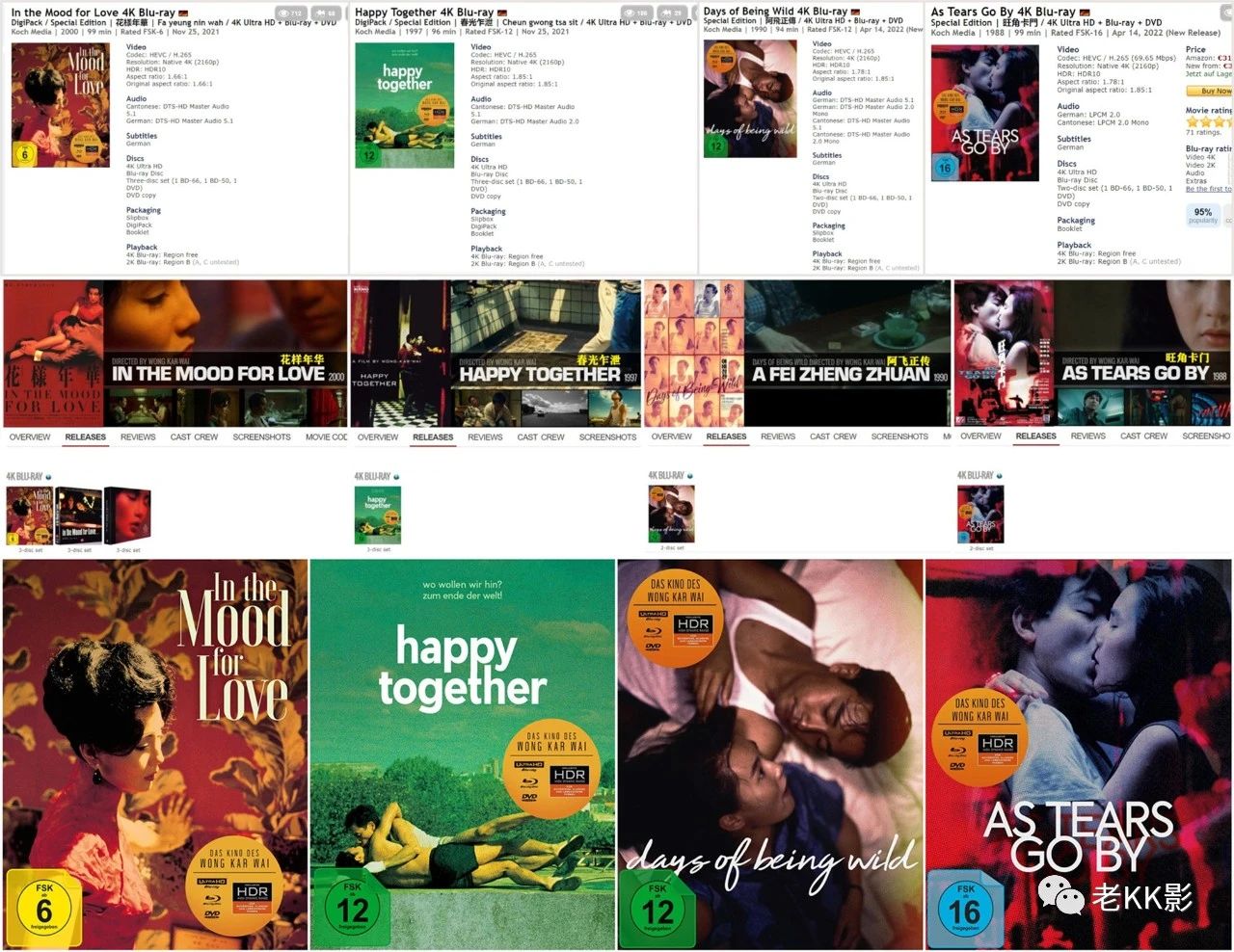从多方面来看,在《都挺好》的画面中,个体困境如何表现?
05-18
浏览量:793
近些年来,国产家庭伦理剧聚焦讨论的话题内容出现了新的变化:从原本传统的婆媳矛盾开始转向对于 内生性问题的探讨。电视剧《小欢喜》《小别离》《 》《少年派》等均在其列。

与此同时, 文化也同样影响了当下电视剧的创作:无论是《欢乐颂》中的樊胜美、《完美关系》中的马邦妮、《安家》中的房似锦,还是《三十而已》里的顾佳,这些角色身上无一不带有 之觞。
有意思的一点是,在当前语境下的电视剧中,出现了这样一类具有以下特征的角色:这类人物多为独立的女性个体,她们大多试图摆脱“吸血鬼”家庭的束缚,最后却又不得不落入回归 的怪圈。

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对比与消费文化的强势助推下,这种立足于女性视角的性别书写极大地满足了国内特定受众的心理需求,由此触发所谓的女性主义的回流。
如果把这种带有鲜明特征的性别叙事看作是彰显女性力量的一种手段,那么这类人物从出走到回归 的矛盾举动则同样投射出当下的一种集体潜意识,即在放有传统与现代价值观两种砝码的天平上,多数人仍将倾斜于传统伦理道德的那一端。

所以,作为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碰撞下应运而生的产物,国产家庭伦理剧中存在着一种极为矛盾的现象,即通过影像叙事与传统伦理的矛盾式弥合来掩盖人物情感维度的断层,隐匿其后的实则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困境。
一个较为典型的例证,就是电视剧《 》。

从《 》对苏大强一家的人物形象描绘中,可以看到现代都市中不同的个体形态,形形色色的人物角色集中体现了当下社会群体所存在的共性特征。
然而影像整体叙事与个体人物的性格弧线之间却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结果,导致影像文本的传播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超强个体”的被动出走与主动回归
如果以经济独立性以及个人能力为标准来评判苏家两代人,那么 无疑是从中脱颖而出的“超强个体”。
就经济独立性而言,当苏明成两夫妻还在靠啃老度日时,身为公司高管的她不仅拥有自己单独的住所,而且还能摆平苏家的经济问题。

而在个人能力方面, 不但凭借自己良好的公司业绩获得了老板的赏识,还用自己的忠诚、果敢与智慧为老板老蒙化解了一场破产危机。
有趣的是,在苏家三个子女当中,这位“超强个体”恰好是位女性。事实上,如若撇去性别的标签,独立人设的兴起恰好是贴合当前现实语境的一种正常现象。从个体化理论的角度来看,独立个体的出现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像教育、社会权利、政治权利、民事权利以及参与劳动市场的机遇、流动过程这些核心性基本社会机制都是以个人为取向,而不所以组织或家庭为取向的。这样,个体化进程就加快了。”
而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当女性拥有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权、劳动权及其他权力,也就是所谓的制度化的个人主义开始落地,那么女性以独立个体的存在形式取代原先依附于集体的生活状态便成为了一种可能,这也是 这一角色得以出现的契机。

认知矛盾:
个体边界的模糊性一般而言,家庭伦理剧侧重展现的是家庭内部的生活场景。然而在《 》中,职场往来也成为了剧情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这部剧里,角色在职场与家庭范围内的人际关系出现了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倒置趋势,但仍未完全脱离费孝通所提出的中国式熟人社交网络。
以 为例,她的身上有两个最为明显的标签,一是独立的职场女强人,二是 中的边缘人,这两个特征恰好到位地概括了人物在职场与家庭两个叙事空间内的状态。

在父母眼中, 是三个儿女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那一个,苏母可以为了给大儿子 凑出国留学的学费而不顾 的意愿强行卖掉她的房间,甚至为了省钱剥夺她上清华北大的梦想;但在面对二儿子苏明成无理的借钱要求时,苏母却总是一味满足他。
而当 求助在一旁目睹一切的父亲时,性格软弱的苏大强总是以视而不见的消极逃避态度来敷衍她。

在两个兄弟的眼里, 则是个冷漠自私的局外人。苏母逝世后,工作繁忙的 到机场接送回国奔丧的 , 看到本该心情沮丧但却依旧冷静克制的 心生不满;甚至在得知苏母出事时两个儿女都未在其身边时,脱口而出指责道“有你们这么当子女的吗”,却不曾考虑到自己也因种种原因而未能陪伴在父母左右。

而对于从小就与 关系不和的苏明成来说,她在他看来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两者间的关系更因牵扯到了二嫂朱丽而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为了避免所在公司停产整顿,当众宣布自己和前来公司开展财务审计的朱丽是姑嫂关系,由此导致朱丽差点失业。
本人也由于此事被苏明成打伤进了医院,这场闹剧最终以报警收场。 在 遭受的冷遇,和在公司亲如一家的人际关系形成鲜明对比,一冷一热交替出现的社交往来开始出现不同于常人的倒置趋势。

尽管在家中并不受人重视,但 在公司却是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她与公司实际控制者老蒙既是上下级关系,也是师徒关系。
两人的初次相识源于 发传单的举动,一段短暂的交谈过程推动了两人日后的密切来往,自18岁后就与亲生家庭断绝关系的 却在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那里收获了自己久违的善意。

作为独立个体的 在家庭与职场间不断切换角色,但以其为中心的社交网络的边界却变得越来越模糊。
如果将剧中关系网络的立足点单纯地总结为从家庭关系出发,那么围绕职场展开的情节内容便被单一地排除在外。
但若将其概括为从纯粹的社会个体关系角度出发,却似乎又难以撇清传统熟人社交的影子:虽然 的当众坦白让二嫂朱丽差点失去工作,但她之后又通过自己的人脉为朱丽保住了工作。

此外,在得知大哥 在美国待业的现状后, 在其不知情的前提下,还是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为他谋划了一份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实则难以厘清该剧对于单一个体的定义。
仅以 一人而言,究竟应将其看作是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中的个人,还是现代语境下的单独个体,仍是一个需要结合具体情境进行仔细辨析的问题。

动机缺失
个体“再嵌入”的荒谬感相较于 与苏明成顺理成章的人生轨迹, 的个人经历却又有所不同。
其以个体身份出走家庭的原因是被迫的,当中还充斥着浓厚的戏剧性色彩:由于重男轻女的苏母强迫 去念她并不喜欢的师范生, 就此与 决裂,从18岁开始便不再拿家里一分钱。

同时,她还和父母签订了一份协议,以舍去父母养老义务的形式来补偿自己在经济方面遭受的损失。而在 “再嵌入” 的过程中,电视剧对于她回归家庭的原因阐释却又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早在 因苏大强养老一事求助 时,她曾冷淡地回应“苏家的事情不要找我”。但在苏大强罹患老年痴呆症之后, 却被苏大强手里那套迟到了多年的习题集所感化,最终为了家庭离开了奋斗多年的职场。

在 做出这一选择之前,剧情内容中仍然掺杂着各种家庭矛盾,却极少有涉及家庭关系修复的情节;此外, 从小的不幸遭遇也是横亘在她与 之间的巨大障碍。
而人物如此突兀的做法,也导致其前后的性格逻辑显得并不自洽。最重要的一点在于, 的做法并不符合个体化理论下“为自己而活”的个人价值观,反之却因带有强烈利他性原则而具有了自我牺牲的意味。
在谈到个体“再嵌入”的话题时,《 》对于 回归家庭的情节安排至今仍饱受诟病。除去上文提及的表象矛盾外,仍有两个与此情节相关的问题值得深究。

其一,“再嵌入”个体的性别设置。在苏家三个子女中, 作为唯一的“超强个体”,却以离开职场的代价回归 。
在角色性别标签的加持下,这一稍显极端的行为的确增强了电视剧的戏剧性效果,然而其传播效果却大打折扣。
换个角度来说,可以将 的人物形象对标为离开职场的全职家庭主妇。由此一来,《 》对于男女平等话题的呈现便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尽管电视剧本身对于苏母重男轻女的观念持否定态度,但其在 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却又带有几分对于女性形象的传统认知。

其二,个体“再嵌入”的动机。
此处所指的动机包含剧中角色行为动机与剧作者创作动机两层含义。
以 为中心的家庭社交网络与职场关系网络存在着冷热倒置的怪象,即便如此, 仍然难以逾越血缘的羁绊。

结语
她回归家庭的选择,更多带有一种妥协的意味。而电视剧强行大团圆的结局设定,同样暗示着着剧作者本身也存在着“血浓于水”的思维定势。
个体“再嵌入”的过程因向血缘关系妥协而带有几分荒谬感。

如果说个体化的具体内涵是指“个体日益从外在的社会约束中脱离出来,这些约束包括整体的文化传统和其中包含的一些特殊范畴,例如家庭、血缘关系和阶级地位”,那么在此处,个体的困境就已经初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