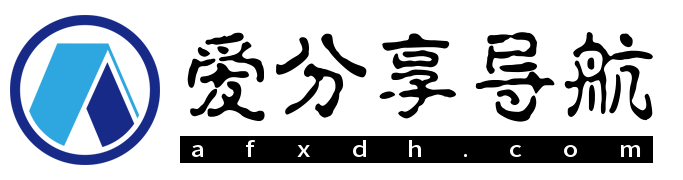三名偶像练习生的梦断一年:承接千元商演,不敢提选秀身份
05-12
浏览量:684

“光合少年”在4月公演中跳Lupin。 (受访者供图/图)
直到2022年4月23日这天,偶像组合“光合少年”成员梓渝还是一位两个月里分文未入的偶像。他少有工作邀约,要不是在当天的组合公演,一些老粉都忘记了他。
他身上有这一行的多重标签:两度出道失败的练习生,承受着行业积弊集中爆发的最后一代偶像 者。2021年,先是 综艺《青春有你3》(以下简称《青3》)因倒奶事件在5月被勒令停播;其后,9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要求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此后,拥挤在 独木桥上的成批练习生退场,成为了小红书美妆区内、抖音带货直播间里、卖场商演中甚至广告拍摄现场的一张张面孔。
梓渝选择了留守。2021年夏天,他经母公司安排,与其他几位练习生组成偶像组合“光合少年”出道。在过去的一年里,梓渝学会了习惯冷清的市场,甚至是商家的抵触。粉丝们也对组合褒贬不一,“内娱之光”与“水平略高于校园舞蹈社团”都成了它的标签。
不过,隔日,他突然因为公演片段上了抖音热搜。这叫梓渝惊喜,在 行业全盛的时代,他也“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而上到抖音的热搜”。但片刻的喜悦后,梓渝深知,留守者的下一个黎明还远未到来。
“我两个月没赚钱了”4月23日,北京海淀区一处小剧场里,一声尖叫来得有些早。“光合少年”刚一亮相,场下就有一位粉丝拉开嗓子开始尖叫。然而,周围无人附和,声音颇为突兀。直到劲歌热舞渐入,占据了剧场一半座位的一两百名粉丝才苏醒过来,尖叫声此起彼伏。
那场公演里,占据歌舞中心位之一的梓渝一次次被粉丝呼喊着名字。跳Lupin时,表演到达了高潮。他喜欢那首曲子里自己的造型:手中挥舞着几斤重的黑色权杖,一条紫色丝绸带围绕脖颈,一副细丝眼镜也重新架回鼻梁。只是太热了,穿着全黑的衬衫与西服外套,暗红色的汗水顺着他的脸滑了下来——这个20岁的偶像刚刚把头发染成了红色。
在 时代落幕后,一些粉丝印象中,梓渝这位“主角”已经淡出一段时间。伊合川是在公演开场时最早尖叫的粉丝,她已是梓渝的“老粉”。2020年,梓渝第一次参加 《少年之名》,伊合川就留意到了他。在她看来,梓渝长得帅,走韩式路线,又有点“小奶狗”的味道,数据也很不错。梓渝中途被淘汰后,她就再没关注过他。直到此次公演的信息发布,她才重新开始关注梓渝。
从《青3》时就对梓渝印象深刻的李凤鸾也已有将近一年没有留神梓渝的消息了。她觉得,尽管“光合少年”并不算火,但也是如今内娱唱跳偶像分赛道上做得比较好的,毕竟他们还坚持在线下举办小型演出。可她也担忧,“这种演出能给他们带来的上升也有限,因为整个舞台的质量和曝光度都不太够”。
公演一天后,南方周末记者在“光合少年”母公司附近见到了梓渝。场外,他素面朝天,穿着商家赞助的国潮夹克,衣服表面已经起了球。
近来两个月,梓渝“主角”的生活里多了几分清闲。除去准备公演与偶尔录制节目,大多数时候,他一觉睡到临近中午。一两个小时的舞蹈基础训练后,他外出去拍要发小红书、抖音的视频、照片,回来做做个人的声乐或舞蹈练习,然后下班。
自从三年前从老家连云港进京做练习生,梓渝很少过这样清闲的日子。但在这一行,清闲不是好征兆,它意味着“身无分文”。“我已经两个月没赚过钱了。”梓渝说。尽管他没有固定工资,但原先靠着各类商务合作,一个月也能赚几千到数万元。然而,2022年多地疫情反复,许多商业机会都打了水漂。他算算,一个月能有两场活动就已经相当不错。
“光合少年”母公司员工荆珏也透露,即便没有疫情,商家对 出身的艺人多有抵触。许多商家都会直接提出,不愿与有 历史的艺人合作。梓渝只能尝试洗刷“ 艺人”的身份,到哪都不敢再提参加两档 综艺的历史。
在疫情与 风波的包夹下,梓渝意识到,“做这一行很大程度需要家里有钱”。据他自称,他的父亲开货车谋生,只能算是普通家庭。为了尽早独立,他四个月没向家里要钱,想尽办法节省开支。
刚刚入行时,他曾觉得,做练习生是明星“预科班”,风光无限,人人向往。不过,出道一年后,他依然住在北京通州区,每天骑电动车在宿舍与位于朝阳区的公司之间往返,这样就能省下约60元打车费。他几乎没有社交生活,公司不愿意他去接触太多圈内鱼龙混杂的人。生活里的枯燥催生了梓渝的主要开支之一:去网吧打游戏。网吧里,充值300元送500元,这800元足够玩一个月。另一项娱乐来源于他为数不多一件的“大件”电子产品:投影仪。晚上回了宿舍,他把手机投屏,看视频消遣。

2022年4月28日,梓渝在公园内拍摄发社交平台物料。 (南方周末记者 姜博文/图)
连3500元房租都要父母接济守到成团出道,梓渝算是个幸运儿。他数了数,他的圈子里,约三分之一的练习生彻底告别了这个行业。荆珏也透露,有许多娱乐公司彻底裁撤了练习生业务。一位前练习生甚至坦言,现在要出道,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公司给练习生们出单曲、拍MV。然而,在他看来,国内公司里没有一个能像韩国大型娱乐公司那样,靠自身能力捧起一个偶像团体并顺畅运营。
由此,无数练习生只能各自散入不为人知的角落。
丁宪孝成为了这一角落中的隐秘者。半年前作为练习生退役时,他只敢接不用出镜的商演单子。正式表演,他也戴着帽子、口罩或是墨镜,不敢把脸完整露出来。
原本 落幕后,他的练习生生涯一度仍有盼头。2021年10月,公司安排了旗下所有练习生做了一场不售票的公演。那天,丁宪孝与将近20名练习生唱跳了一个半小时。尽管一直没有闯出太大名气,但台下有自己的应援呐喊,约500名观众里,他还认出了一些粉丝,心里“蛮激动”。表演结束,公司也对练习生们说,此次公演将是一次实验,要是效果好,接下来也许会走日本偶像组合AKB48的路子,把公演固定下来,公开售票。“所以我们本来以为后面会有更多上舞台的机会”。
可公司突然停训了大部分练习生。丁宪孝也是其中之一,他一度处于歇业状态。在他看来,这“说白了其实就是公司没钱”。
此后大半年里,他都在要求与公司解除此前签订的十年长约,然而公司始终不同意。不得已,丁宪孝一边继续扯皮,一边在上海做舞蹈代课老师,顺便跑商演。商演时,为了避免与公司发生肖像权等纠纷,他得“掩面”演出。如同风筝一般,他身后挂着一根线,线的那一头被公司紧紧捏着。
没有签约公司的个人练习生罗义喆无牵无挂,在斩断过往时,他轻松得多。他先是做了一个月的密室逃脱演员,旋又变成自由职业者,拍广告,也接商演舞蹈。拍广告属于“不那么累,但赚得比较多”的职业,对于他这样名气不算大的人,每次1500到3000元不等;而一场商演,报酬则约1000元。他也打听过,一些常跑商演的“老活动人”,一个月接个十几单,生活费就有了着落。
在罗义喆看来,新工作要比练习生好得多。做练习生时,练习生们之间总有“若有若无”的竞争关系,可商演的活儿“没有任何压力”。他也见过那些至今没有离开公司的练习生出来接单,一单报酬本就1000元不到,还要与公司分成,最后到手不过几百元,“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可这份喜悦并不长久。疫情搅乱了罗义喆的新事业。有一回,他接了一位知名香港艺人巡回演唱会的伴舞单子,结果巡演因疫情只开了澳门一场。2022年初,上海又暴发疫情,他整日坐困出租屋内,就连做自媒体、推广产品的广告费也挣不到——快递停运,产品送不到他手上。罗义喆抱怨,若是前几笔活动的费用再不结清,他就得管父母要钱支付房租了。
丁宪孝已经向父母伸了手,4月的房租就是父母接济的,5月呢?丁宪孝拉不下脸开口再要。2022年回到上海,遇上疫情,他只靠代课赚了2000多元,也就是正常时候月入的五分之一,连付每月3500元的房租都不够。此间,有中介招聘方舱的保安与环卫工,工作6小时,休息6小时,开价1500元一天。报酬诱人,他仔细考虑过,但内心实在抵触岗位,父母也反对,他没报名。
如今如此惨淡收场,丁宪孝感慨,要是能早点预知 的落幕,他不会拖到此时才退场:早些出来跑商演、做舞蹈老师挣钱不好吗?
罗义喆倒是至今还会想想成团出道的美事。他记得有一回拍广告,品牌方拉来了几个女团成员。拍摄时的一段舞蹈动作,他与几个舞蹈演员都没有做错,反而是女团团员们屡屡出错,叫全场的人都在等她们。
那时,他不由得想:“为啥这个主角不是我?”

“光合少年”服装间。 (南方周末记者 姜博文/图)
“每天活在《甄嬛传》里是什么感觉”在 这一行里,没有练习生不做“主角”梦。回想起来,罗义喆第一次接近成为“主角”的机会,是给父母下跪才换来的。
2018年,他跪了父母,等二老点头,才签了北京一家娱乐公司,算是入了行。那年,《青1》方兴未艾,海选时,罗义喆没选上,随后就被公司遣散,老老实实离开了公司给练习生在北京朝阳区租的一栋别墅,回了上海的大学校园。
在 综艺炙手可热的2018-2020年,很少有人会留意这次不起眼的铩羽而归。据红星资本局,《偶像练习生》于2018年4月6日收官,截至4月8日,总播放量达到28.3亿,同名微博话题阅读量达到134.9亿,相关微博话题盘踞微博热搜榜高达577次;《创造101》于2018年6月23日收官,截至6月23日晚,总播放量超过44.4亿。而据FUNJI与36氪联合发布的榜单,2020年,《青2》也位列年度热门综艺榜榜首。练习生血液为此总在快速更新。罗义喆返沪不到一年后,16岁的梓渝也从江苏老家被选进京。据他回忆,那时,他不过是个播音艺术生,老板无意中看见了他的照片,一眼就相中了他,要拉他入行。
梓渝周围,同龄人都觉得做练习生“刺激”“帅”,他也觉得被人唤作练习生“很光荣”。于是,大笔一挥,合同签就。
他很快就比许多人走得更快、更远。唱跳培训了半年多,他就在地铁上接到了公司通知入选 节目《少年之名》的电话。他懵了:自己怎么就选上了?公司练习生考核,他唱跳周周倒数一二;去剧组试戏,他自我介绍都磕磕巴巴;《少年之名》三面,他觉得评委尚雯婕都没有看他一眼。
后来,这场意外入选也被证明是个颇有些“范进中举”意味的结果。2020年3月,选手正式进组。数月时间里,梓渝杀入节目50强。微博上,他涨了粉;背景采访播出那天,有20个属于他的站子(即由粉丝成立的明星官博或后援会)“开张”;从酒店去往录制基地的路上,他开始被站姐们的闪光灯晃到睁不开眼;酒店里,他透过窗户看见有粉丝安装着屏幕的车,放着祝他生日快乐的视频。
“我也有这样的一天,蛮火的啊。”他想,自己不再是个素人了。
很快,悲喜两重天。他在50进20时被淘汰。霎时,“天都黑了”。台上,他直接哭了起来,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被淘汰。
从《少年之名》出局时,梓渝离家已有7个月。他身心俱疲,休假回家。可 之路根本无法停歇,前脚到家,后脚《青3》便开始海选。在家歇了才两周不到,梓渝又返了京,第二次通过选拔进组。
这回压力更甚,疲惫被放大到了极限。一次背景采访结束,已是凌晨3点,工作了11个小时的梓渝困到在地板上睡着了。他回想,不光是录制人困马乏,舞台以外的人际关系更心累。 渐渐演化成一场“宫斗大戏”。
一位参与节目的选手说,下了舞台,跟谁玩,身边朋友是谁,都得仔细考虑。“你想想,你每天都生活在《甄嬛传》里是什么感觉?让你生活半年,你累不累?”
一个例子是,选手们也分三六九等。在前述选手看来,会有选手因为另一位选手不够火而在现场互动时不说太多的话;也有位次低的选手去蹭位次高的选手热度,“干什么都天天蹭火的”。那种不分阶层的兄弟之情,他曾亲身经历过,只是那样的时刻不多。

“光合少年”在练舞厅内训练。 (南方周末记者 姜博文/图)
“词儿太狗血,记不住”累,太累了。这也是罗义喆在2020年入选一档 综艺,第二次冲击主角时的感受。节目开始前,所有选手高强度集训了4个月。有人练得膝盖积水,感冒、发烧者更是大有人在。即便如此,也没人敢偷懒,因为到处都安了摄像头,节目组始终有人盯着他们。
这或许是许多练习生的心态,无法忍受这极致的疲惫,却难舍 舞台。前述综艺后因自身原因在录制前停了,所有人都白练了4个月。听闻此事,一同在该综艺组内的丁宪孝觉得崩溃。公司暗示过他,考虑到年龄问题,这可能是他最后的 机会。此前,他曾双双入选《青3》与该 。尽管更喜欢前者,他却因为听从公司安排去了后者。如今,前者已经开播,后者却胎死腹中。
他们并不知道,在《青3》,梓渝的日子也不好过。他觉得,选手与选手、与选手管理者之间彼此“斗争”了几个月,失掉了大部分的灵性与笑声。进组半年后,他时时刻刻都想出去。
最终,被淘汰时,梓渝脑子里一度只剩下一个想法:“如果再有 ,别叫我”。荆珏说,就连公司都决定,短期之内不会再选送他去 。
“中举者”与“落第者”都未曾想到,仅仅几个月后,因为倒奶事件,《青3》的舞台就崩塌了。
罗义喆坦承,得知《青3》停播,站在对手的角度,他最初有些开心,毕竟自己参加的节目早就宣告死亡。但当养成系 节目随后完全停播,他很是矛盾。他见过太多“花瓶”被硬塞进节目,行业该整顿;但在那之外,罗义喆还生出一种一直追不到的心上人突然死了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我是真的没路走了。”
梓渝难以想象那些走到《青3》最后关头的选手的心境。他庆幸自己在 落幕前全身而退,假如自己那时仍然在组里,恐怕“真的会绝望”。
所幸公司规划没有受 落幕的影响。2021年6月,“光合少年”出道。梓渝依然抱有希望,纵使因4月23日的公演片段上了抖音热搜,他也觉得他只是在做偶像路上迈出了第一步。时机恰当时,他想站上更大的舞台,开演唱会,或是上大型综艺。
“他(梓渝)只是缺一次露面的机会。”荆珏对此总结道,而这个机会也不一定得是一档节目。自媒体时代,只要能让内容传播起来的都是机会。
但在行业寒冬之下的生存并不容易。荆珏说,4月的公演办下来,场租一天就要一万元。另外,北京防疫政策严格,外地粉丝进京困难,188元一张的票,只有一两百名粉丝到场,公司盈利艰难。他们正考虑去成都办下个月的公演。
4月28日,梓渝本要去一个剧组试戏,因为疫情,试戏改为拍摄剧情片段提交。在剧里,梓渝试演的角色是校园高材生。休息室里,他一面看着剧本,一面感叹“词儿太狗血,记不住”,可他不能拒绝,“生活中有很多不得已”,而他只能“干一行,爱一行”。他甚至担心,自己试戏时显得随便、慵懒了,万一被谁看到,传出去也败公司的名声。
那天晚上,梓渝离开公司时,一楼一间房里传来了音乐声。荆珏猜测,也许是新练习生在练习舞蹈。公司新签约了一批练习生。梓渝走向房间,突然,他在门前顿顿足,想了想,最终还是没有推开那扇门。
(何豆豆对本文亦有贡献,文中荆珏、丁宪孝、伊合川、李凤鸾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姜博文 高伊琛 南方周末实习生 戴纳 张校毓